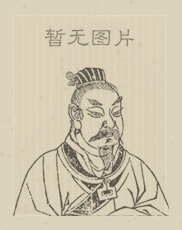
早年生涯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五月二十二日,李淏出生于汉城(今首尔)庆幸坊,其父为绫阳君李倧(后来的仁祖),母亲为韩氏(后来的仁烈王后)。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三日,李倧发动“仁祖反正”,推翻光海君的统治,成为新任朝鲜国王,李淏也成为王子。不过他还有长兄昭显世子李𪶁,所以他以嫡次子的身份,于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被册封为“凤林大君”,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迎娶仁祖反正功臣张维之女(后来的仁宣王后)。与此同时,仁祖还在於义洞为他营建府邸,修了两年以上,规模“极其宏丽”,时人形容为朝鲜王朝开国以来“私家未有其比”,故此举颇受舆论非议。
李淏五岁开始读书,十岁起师从南人学者尹善道三年之久,李淏后来称赞他“善于训诲”,并说“予之解蒙,实赖此人之功也,予常不能忘于怀”。有一次,李淏问他处身之方,尹善道回答:“‘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句),难道不是千古名作吗?”李淏遂感悟到韬光养晦之道,以此处身。十七岁时,又有西人学者宋时烈当了他的师傅。后来宋时烈成为李淏晚年的重臣。
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率清军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历史上称为“丙子胡乱”。凤林大君李淏偕弟弟麟坪大君李㴭及世子嫔姜氏等王室眷属逃往江华岛。翌年正月二十二日,清睿亲王多尔衮率军进攻江华岛,朝鲜防线迅速瓦解,李淏先召集分备边司诸臣,商讨对策,派李敏求去侦察敌军,然后“披甲募兵”,在江华府城南门外遭遇清军,迅速败退。多尔衮派人到城下劝降,否则屠城,李淏派尹昉前去交涉,然后决定前往清营投降,多尔衮以礼相待,在晚上与多尔衮“联骑入城“。其后,李淏按多尔衮要求,给南汉山城中的仁祖写信。仁祖得知江华岛失守、李淏等被俘之事后,被迫同意出城投降。正月三十日,仁祖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李淏就与其他江华岛俘虏站在受降坛下西侧,目睹了这耻辱的一幕。
成为储君
丙子胡乱结束后,李淏尚不能立刻与父亲团聚,而是与妻子及兄长昭显世子一起被押送到清朝都城盛京(今辽宁沈阳)做人质。崇德六年(1641年)八月至九月跟昭显世子一起随皇太极前往锦州,观察明清松锦大战。李淏自称在入质盛京之时,臣民就认为自己更贤德而归心,不过也有说法是终日饮酒嬉戏,无心学问。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昭显世子随清摄政王多尔衮出征,李淏则于五月七日回到朝鲜,七月九日又北上清朝,并赴北京参加顺治帝的登极大典。其后,多尔衮召见昭显世子与凤林大君李淏于武英殿,允许朝鲜人质回国。其中昭显世子先回,而李淏则于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二十六日获准东归。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二十六日,李淏离开北京,五月十四日,抵达汉城。此前四月二十六日,他的兄长昭显世子去世,仁祖无意按惯例立昭显世子之子为王世孙,而打算立李淏为王世子,此举遭到多数大臣反对,唯独领议政金瑬和洛兴府院君金自点支持。尽管如此,仁祖在得到清朝使者的首肯后,还是强行于九月二十七日立李淏为王世子。清廷则派遣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礼部郎中朱世起等前往朝鲜,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三日正式册封李淏为朝鲜国王世子。
即位为王
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初八日,仁祖病危,李淏非常悲痛,差点咬断左手手指,幸得麟坪大君李㴭相救而没有断骨,随后仁祖升遐,李淏于五月十三日即位于昌德宫仁政门,是为孝宗。清廷派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撒尔岱携诰命、冕服等物前往朝鲜,于九月初七日正式册封孝宗为朝鲜国王。
孝宗继位之初,朝中掌权的西人党分为四党,分别是洛兴府院君金自点为首的洛党、原平府院君元斗杓为首的原党(以上由勋西派分化而来)、金集等“山林”儒者势力为首的山党和金堉等汉城政界官僚为首的汉党(以上由清西派分化而来)。其中势力最强的是洛党。孝宗即位后,起用山党人士,任命金集为礼曹参判、大司宪,宋浚吉为司宪府执义,宋时烈为司宪府掌令,还召见了已经隐居的斥和派重臣金尚宪,展现了与仁祖朝迥然不同的气象。另一方面,山党对仁祖反正功臣势力的弹劾也开始了,金自点被流放,元斗杓被罢官。其后山党和汉党又围绕实施大同法和选拔人才的问题而产生矛盾,孝宗选择支持金堉为首的主张大同法的汉党,其深层次原因可能在于山党想给愍怀嫔翻案,危及孝宗的王权合法性。到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金尚宪、金集、宋浚吉、宋时烈等山党人士全部离开朝廷。
另一方面,孝宗在对清关系上也进行调整。仁祖末年,金自点为首的亲清派洛党专权,强制要求所有场合使用清朝年号。孝宗继位后,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传递出反清的信号。另一方面,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武力推翻清朝,恢复明朝,并一雪丁丑下城之耻。他即位后,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操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他曾在经筵中强调汉武帝能雪平城之耻,故优于汉文帝,由于在儒家史观中,汉文帝的评价高于汉武帝,所以他的这席话遭到在场儒臣的反对,但也有人悟出了“北伐”的深意,如宋时烈在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所上封事中提出“修政事以攘夷狄”的主张,就是对孝宗“北伐论”的回应。
巩固统治
金自点被流放后,其心腹译官李馨长密告清朝,称孝宗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并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仁祖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上奏汇报“倭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士兵来防备日本,同时又请求将漂流汉人船只送到倭馆,惹恼了清朝。清摄政王多尔衮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顺治七年(1650年)春的六使诘责事件。史载当时“人情震惧”、“朝野汹汹”,传言清兵压境,孝宗听说后也“大惊忧,达夜不寐”。他起用已被罢官的元斗杓为远接使,领议政李景奭也自告奋勇,前去义州侦察情况。结果清使雷声大雨点小,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以李景奭和撰写“倭情”奏文的赵䌹被流放白马山城了结。清使还顺便为多尔衮提亲,孝宗遂以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一场外交危机得以化解。
顺治八年(1651年)十一月,仁祖后宫赵氏诅咒案东窗事发,孝宗趁机挖出了金自点为首的阴谋集团,粉碎了他们的未遂政变。金自点从流放地光阳押赴汉城,凌迟处死,废贵人赵氏被赐死,孝宗由此巩固了王权。孝宗以汉党金堉、郑太和轮流为领议政,主导政局,同时辅以原党及南人的势力,这一政治格局维持到孝宗末年。
孝宗稳固了权力以后,为了实现北伐目标,积极扩军练兵,充实财政与军备,实行了推刷奴婢、营将制等政策,但收效不大。更严峻的现实是在小冰河期的环境下,孝宗统治下的朝鲜天灾频仍,连续六七年粮食歉收,引发饥荒,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更是到了“风旱饥馑,近古所无”的地步。同时,他以北伐为目标的财政与军事计划不仅难以落实,也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顺治十二年(1655年)孝宗为慈懿王大妃赵氏(庄烈王后)营建万寿殿时,曾召见了一些家属死于丙子胡乱的大臣,稍微透露北伐之意,但都“皆邈然无以为意”。因此,孝宗后期经常叹息“日暮道远”,流露出深深的挫败感。
赍志以殁
孝宗赐宋时烈密札顺治十五年(1658年),孝宗所倚重的能臣金堉病重,九月去世。孝宗对于其他重臣不甚满意,认为元斗杓“不无其才,而气质素欠从容,似难为精细之事”,沈之源“贤而无才”,李厚源“多病不出”,郑太和虽然“有智有虑识事务”,但“不欲担当重事”。所以在当年九月,孝宗重新起用宋时烈、宋浚吉等“山党”士人,提拔宋时烈为吏曹判书,宋浚吉为大司宪,后擢为兵曹判书。顺治十六年(1659年)三月十一日,孝宗单独召见宋时烈于昌德宫熙政堂,和盘托出他北伐的抱负。孝宗自信“熟知彼中形势及山川道里”,因此对清朝没有“畏慑之心”。他的北伐论是建立在“满清崩溃论”的基础上,即他判断“彼虏有必亡之势”,依据如下:
皇太极兄弟众多,顺治帝兄弟稀少;皇太极时人才济济,顺治帝时都是庸劣之辈;皇太极时崇尚武事,顺治帝时日益汉化,武事渐废;顺治帝“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
他认为北伐的可行性在于:
中原豪杰义士会群起响应;满清不尚武事,辽沈防备空虚;朝鲜向清所贡岁币都在辽沈,北伐期间可资军用;丁卯、丙子胡乱中有数万朝鲜俘虏,可为内应。
因此,孝宗计划在十年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等待清朝内乱,然后出兵直抵山海关外,强调“大概今日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能有为矣”,并认为大臣们都反对北伐,只有宋时烈才是唯一值得共同商议北伐的人。宋时烈虽然也高唱“内修外攘”,但认为“内修”是“外攘”的前提。他在《丁酉封事》中指出要北伐首先在于“正君心”,不赞成急进的财政与军事计划。在接受孝宗单独召见时,仍然大谈“格、致、诚、正”才是当务之急,强调“养民足食”;而孝宗则一心“养兵”,将“养兵”与“养民”的协调搁置一边,将来再议,因此君臣二人看似鱼水相得,实则同床异梦。
这次召见不久后的三月二十六日,孝宗梦见金自点提剑闯入寝宫。四月,孝宗的鬓角就长了脓包,不久蔓延脸部,以致不能开眼。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初四日,医官申可贵给孝宗脸部施针灸时不慎扎进血管,血流不止,孝宗随即升遐于昌德宫大造殿,享年四十一岁。死后庙号孝宗,谥号宣文章武神圣显仁大王(后加谥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明义正德大王),葬于宁陵。清朝赐谥“忠宣”,朝鲜内部不用。世子李棩继位,是为显宗。